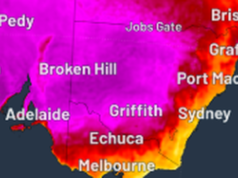攝影師記錄大屠殺前後猶太人的生活
愛德華·塞羅塔(Edward Serotta)像經理一樣走遍大屠殺倖存者及其家人的房間,檢查他們是否有足夠的食物、飲料和陪伴。他和一些人坐在一起,拍拍其他人的背,親吻他們,並確保維也納猶太社區中心的每月一次會議順利進行,儘管維也納警察在外面站崗以防萬一。大約 80 人參加了上個月在 Café Centropa 舉行的猶太新年前聚會,追隨塞羅塔先生的獨特項目和成就:Centropa,他創立的非營利組織,旨在記錄中歐和東歐猶太人生活的消失。在數十名研究人員和無數次該地區旅行的幫助下,Serotta 先生和 Centropa 創建了一個數字檔案,其中包含在 20 個歐洲國家進行的 1,230 次採訪,總計約 45,000 頁的證詞。該檔案包含超過 25,000 張照片。 “他們每個人背後都有一個故事,”塞羅塔先生說。 “大屠殺是人類最大的罪行,只要有目擊者,這些故事就必須被講述和記錄。但還有另一個章節,其中每個人在前後都擁有精彩的生活。”他在維也納為 Centropa 找到了資金,部分來自文化部,部分來自奧地利大屠殺賠償機構總經理漢娜·萊辛 (Hannah M. Lessing)。 “我們立即聯繫了——我們知道我們想要什麼,也知道我們想為倖存者做些什麼,”萊辛女士說。 “正如一位倖存者所說,我和艾德有共同點:‘每個人都問我們是怎麼死的。沒有人問我們是怎么生活的。’” 93 歲的菲利普·G·科恩瑞奇 (Philipp G. Kornreich) 就過著這樣非凡的一生。出生於維也納,1938 年隨父母逃往裡加。納粹到來後,一家人被蘇聯人送到哈薩克斯坦半沙漠的一個貧窮的集體農場。直到 1947 年,經過八週的火車旅行後,他才被允許返回維也納,隨後他最終成為雪城大學電氣工程教授。現在,他住在維也納——“距離我開始的地方只有兩個街區”,他說——來到 Centropa 咖啡館,參與“這個現在很小的美好猶太社區”。麗塔·道伯也在場。她的父母出生在波蘭的切爾諾維茨(現在的烏克蘭切爾諾夫策),並在戰爭中倖存下來。 “她一直不願意談論這件事,直到她生命的最後一刻,”她補充道。 “對於這些人中的大多數人來說,生活是一本書。埃德幫助他們講述。” 晚上晚些時候,塞羅塔先生前往敖德薩,在那裡他為烏克蘭教師舉辦了一個關於在戰時國家使用 Centropa 教材的研討會。然後他前往烏克蘭東部的博赫丹諾夫卡,1941-42 年羅馬尼亞軍隊佔領敖德薩後,在那裡殺害了多達 54,000 名猶太人。塞羅塔有一頭捲曲的灰色頭髮,視網膜修復得很差,還有輕微的跛行,在如此嚴格的日程安排下,他的牙齒可能會變得更長一些。 “一個 76 歲、半盲、腿傷的同性戀者穿越戰區尋找猶太作家居住的城市的整個想法似乎有點瘋狂,”他承認。但他對此並不太擔心。他出生在佐治亞州薩凡納的一個猶太小社區,他的父親在那裡經營一家靠賒賬的珠寶店——“折扣 5 美元,每週 5 美元,”塞羅塔說。房子裡沒有書,但他的父親喬治每個週末都會帶著兒子去看船隻進港。他的父親打電話給水手,詢問是否可以帶兒子上船去旅行。塞羅塔先生回憶說,有一次以色列沙洛姆號船正在航行,他的父親帶一名水手回家吃安息日晚餐。這一切讓他產生了旅行的願望,正如他所說,“只是旅行的幻想”。搬到田納西州並在田納西大學學習市場營銷後,塞羅塔先生搬到了洛杉磯,在音樂行業的邊緣工作,並對攝影產生了持久的興趣。他結婚四年,然後離婚,後來出櫃了。 1980 年,他搬到亞特蘭大,賣辦公用品,心情鬱悶,在菲利普·羅斯 (Philip Roth) 倡導的鐵幕後的歐洲作家那裡尋求安慰。因此,他前往布拉格、維也納和布達佩斯,出售有關失敗的反共起義和奧地利不為納粹感到難過的獨立文章。 1986年,他來到了布達佩斯,然後去了南斯拉夫和羅馬尼亞。他的自由職業有足夠的市場來維持他的生存,所以“然後我開始拍攝猶太人”,他說,並從羅馬尼亞安全局秘密警察那裡獲得了一份 300 頁的文件,後者懷疑他是一名西方特工,在這個反猶太主義惡毒的國家煽動麻煩。 1988年初,他賣掉了在亞特蘭大擁有的一切,除了書籍,再也沒有回到美國。他搬到布達佩斯,在那裡他開始了工作,最終創立了 Centropa,出版了第一本猶太人生活照片集《走出陰影》,然後去了布拉格、柏林,最後去了維也納。他還報導了 1989 年柏林牆的倒塌,然後報導了 20 世紀 90 年代初波斯尼亞塞族圍困薩拉熱窩的事件。但他說,吸引塞羅塔先生的是猶太人生活不斷消失的故事,但沒有人記錄下來。 “這些國家都有令人著迷的重新發現和自我發現的故事,所以我必須在那裡記錄它們,”他說。 Centropa 檔案館現已被美國大屠殺紀念博物館收購,作為其永久收藏的一部分。 “這是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資源,有助於完善我們對中歐和東歐的了解,”博物館策展事務總監扎卡里·保羅·萊文 (Zachary Paul Levine) 說。萊文先生說:“我經常向 Centropa 尋求幫助,找到一些證詞來幫助我了解地球上的生命是什麼樣子。” “埃德將個人文件和證詞與照片和背景結合起來的方式讓我非常滿意。”返回維也納社區中心後,Tanja Eckstein 描述了她如何來到 Centropa。她的父親出生於 1905 年,是猶太人,在父母被謀殺後在達豪集中營倖存下來,但“他什麼也沒告訴我,”她說。 “他經歷了巨大的創傷,拒絕來維也納”,在東柏林過著孤獨的生活。 “我對猶太歷史感興趣,因為我沒有家人,”她說。在維也納的猶太小社區,她聽說了塞羅塔先生以及他對大屠殺倖存者及其對生活和村莊的記憶的不切實際的興趣。 “我告訴他我的故事,”她說。 “他給了我一個大麥克風和一台錄音機,然後說,‘繼續吧。’”埃克斯坦女士在該地區進行了 71 次採訪。 “你會更接近這些人,”她說。當他們問什麼時候能再次見到她時,“埃德說,‘讓我們把所有來電的人聚集在一起。’”2006 年的第一次會議有美國、英國和以色列大使參加。 “然後埃德說,‘我們每個月都這樣做吧。’”這就是 Café Centropa 的誕生,當晚 90 歲的大屠殺倖存者、現在的寡婦基蒂·施羅特 (Kitty Schrott) 出席了這家咖啡館。 “很高興認識朋友,了解猶太人,”她說,“而不是坐在家裡悲傷。”
已发布: 2025-10-16 02:51:00
来源: www.nytim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