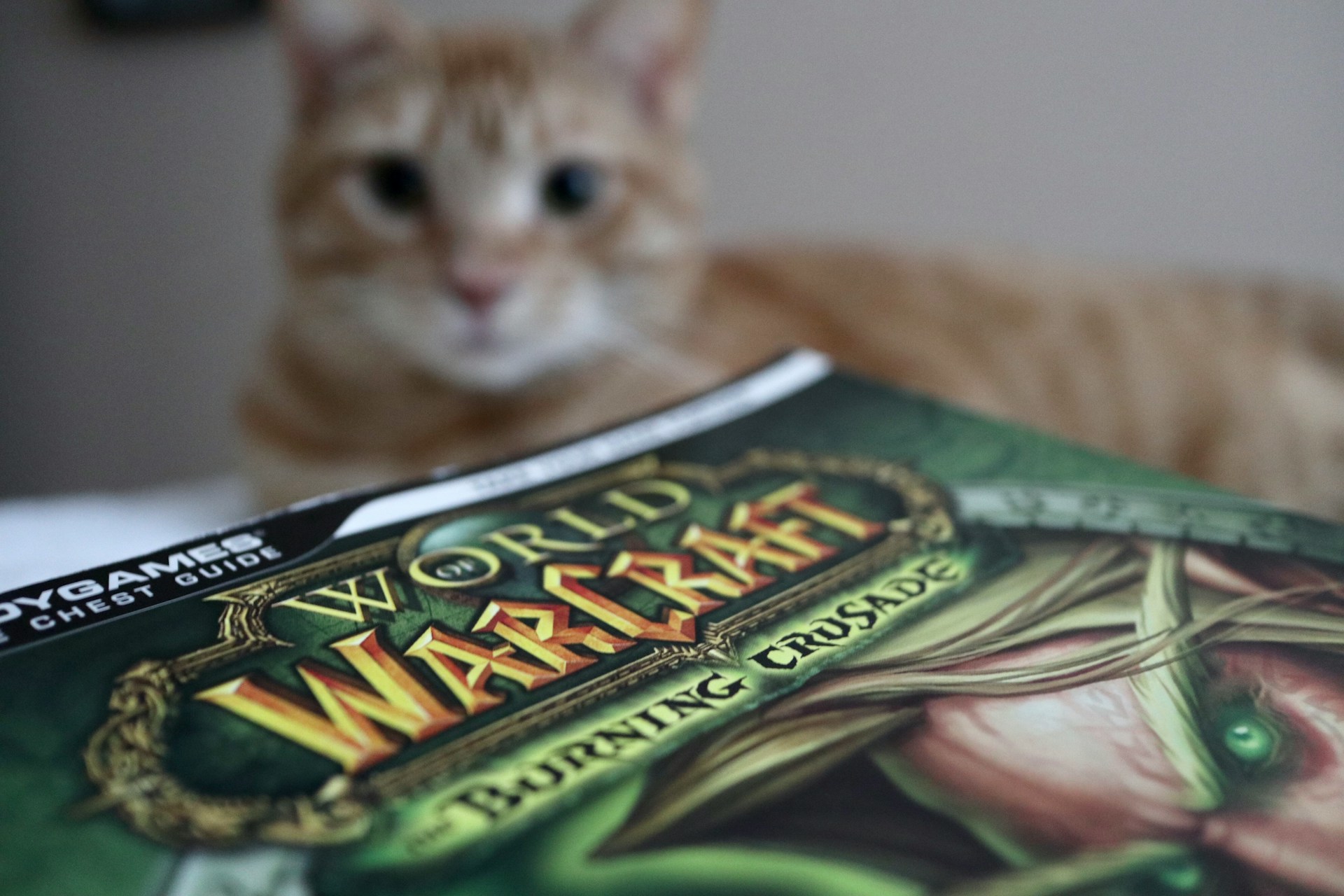在印度北部城市勒克瑙的一個公車站,一張張焦慮的臉孔訴說著他們的故事。
曾經為了工作而來到印度的尼泊爾人,如今正匆匆越過邊境返回,因為尼泊爾正遭受幾十年來最嚴重的動亂。 「我們要回祖國了,」一名男子說。 “我們感到困惑。人們都在要求我們回來。”
本週早些時候,尼泊爾總理卡·帕爾馬·夏爾馬·奧利在社交媒體禁令引發的衝突中已造成30人死亡後辭職。雖然禁令後來被撤銷,但Z世代領導的抗議活動仍在繼續。全國實施宵禁,士兵在街上巡邏,議會和政客的住所被縱火焚燒。奧利下台後,尼泊爾政府不復存在。
對於像薩羅伊·內瓦爾巴尼這樣的移民來說,選擇是殘酷的。 「家鄉有麻煩,所以我必須回去。我的父母在那裡——情況很嚴峻,」他告訴BBC印地語頻道。其他人,如佩薩爾和拉克什曼·巴特,也表達了同樣的疑慮。 “我們什麼都不知道,”他們說,“但家鄉的人要求我們回來。”
對許多人來說,返鄉之路不僅僅關乎工資或工作——它與家庭紐帶、不安全感以及長期以來塑造尼泊爾人生活的遷徙節奏息息相關。畢竟,在印度的尼泊爾人大致可分為三類。
首先,是那些離開家人,在印度各大城市從事廚師、家事、保全或低薪工作的移工。他們仍然是尼泊爾公民,四處遷徙,沒有Aadhaar(印度的生物識別身份證),並且經常被剝奪基本服務。這就是為什麼他們有時被稱為季節性移民。
其次,是那些帶著家人搬遷到印度,在印度建立生活,通常獲得身分證,但仍保留尼泊爾公民身份和家鄉紐帶的人,甚至會回來投票。
第三,印度有尼泊爾裔公民──他們是18世紀至20世紀早期移民潮的後裔──他們紮根於印度,但仍聲稱與尼泊爾有著文化上的親緣關係。
根據最新官方數據,尼泊爾也是印度留學生最多的國家,在印度約4.7萬名留學生中,尼泊爾學生超過1.3萬人。此外,還有許多其他尼泊爾人跨越1750公里(466英里)的開放邊境,尋求藥品、物資或探親,這得益於1950年簽署的和平友好條約和強大的社會網絡。
加德滿都特里布文大學的凱沙夫·巴什亞爾表示,進入印度勞動市場的尼泊爾新移民通常年齡在15至20歲之間,但整體平均年齡為35歲。失業和日益加劇的不平等現象推動了移民潮,尤其是在貧困人口、農村人口和教育程度較低的人群中,他們的勞動參與率本來就很低。
「他們大多來自貧困家庭,在北阿坎德邦的建築和宗教場所、旁遮普邦的農場、古吉拉特邦的工廠以及德里及其他地區的酒店工作,」巴什亞爾博士告訴我。
這股穩定的年輕移民流構成了印度一個規模龐大、但基本上不為人知的勞動力大軍。
「由於邊境開放,很難確切知道在印度工作和生活的尼泊爾公民人數,但估計約為100萬至150萬,」愛丁堡大學南亞政治人類學家傑文·夏爾馬說。
尼泊爾對其移民的依賴程度令人震驚。
2016-17年,匯款佔尼泊爾GDP的四分之一以上,到2024年將達到27-30%。超過70%的家庭收到匯款。匯款如今佔家庭收入的三分之一,高於30年前的27%。其中大部分匯款來自在海灣地區和馬來西亞工作的尼泊爾公民,印度貢獻了約五分之一。所有這些使尼泊爾成為全球第四大匯款依賴國。
「儘管印度匯款的人均匯款遠低於前往海灣地區或東南亞的移民,但印度的匯款卻流向了尼泊爾最貧困的家庭,」夏爾馬教授表示。 “如果沒有印度的匯款,尼泊爾的經濟將遭受重創。”
然而,儘管在印度的尼泊爾移民在經濟上舉足輕重,但他們的生活往往岌岌可危。
2017年在馬哈拉施特拉邦進行的一項研究發現,尼泊爾移民擠在骯髒的共用房間內,衛生條件極差,在工作和診所經常遭受歧視。酒精和菸草使用率很高,性健康意識低。社群網路既是他們的生命線,也是他們的負擔:它們提供了工作、住所和小額貸款,但也強化了他們對一小部分人的依賴,限制了更廣泛的機會。
另一項在德里進行的研究發現,尼泊爾移民「工作是為了基本生存,而不是為了提高生活水平」。
以孟買保全Dhanraj Kathayat為例。 1988年,他來到印度,當時還是個尋找工作的年輕人,之後輾轉於納格浦爾、貝爾高姆、果阿、納西克等城市,最後定居在了這座西部大都市。他最初從事的是駕駛工作,但在過去的16年裡,他一直在做建築保安,這份工作雖然能提供一些安全感,但晉升空間有限。
「我沒怎麼想過家鄉的狀況,」他告訴我。 “尼泊爾的失業率很高,即使是受過教育的人也很難找到工作。所以像我這樣的人不得不離開。”
卡塔亞特先生的家人仍留在尼泊爾。他有兩個女兒和一個兒子,都在上學。在印度,他繼續當保安,收入勉強維持生計,還能寄點錢給一年只見一次面的家人。
“這麼多年過去了,我自己並沒有太大的發展。有些移民發了財——那些去了韓國、美國或馬來西亞的人。不像我們這樣的人。”
這種隱形狀態是否延伸到政治層面,目前尚無定論。
幾乎每個尼泊爾主要政黨都在印度城市設有姊妹組織,通常由當地委員會運營,利用這些僑民籌集資金、動員支持,並將政治觀點傳遞回國。
「在印度的尼泊爾移民工人在祖國仍然積極參與政治活動。儘管貧窮且邊緣化,但這些移民在塑造本國政治方面發揮著巨大的作用。他們的影響力在王室接管期間尤為明顯,當時印度的流亡領導人嚴重依賴他們的支持,」夏爾馬教授說。
其他人,如巴什亞爾教授,則對此持懷疑態度。
「1990年之前,他們(移民)主要為政治領導人提供住所和經濟支持;後來,在毛派運動期間,他們也提供了積極的支持。如今,他們的政治影響力已微乎其微。有些人仍然跨境投票,尤其是在地方選舉中,但他們在政策辯論中的作用仍然微乎其微,」他說。
與許多受經濟壓力束縛的移工不同,在印度的尼泊爾學生似乎更善於表達、更積極參與,也對未來充滿希望。
來自德里的學生阿南特·馬托告訴BBC印地語頻道,如果他在尼泊爾,他會加入抗議活動:「憲法至高無上,」他一邊抱怨領導層的真空,一邊相信現在是「重建」的時候了。
另一名學生特克拉伊·柯伊拉臘擔心家人,但仍然保持樂觀:「我對未來充滿希望,」他說。
另一名學生阿卜哈·帕拉朱利說:“如果我在尼泊爾,我會和朋友們一起參加抗議活動,儘管我不支持破壞私有財產……我們希望出現一位更好的領導人。”
分析家認為,加德滿都的每一次暴動都會加劇抗議浪潮,將年輕人推向印度的非正規經濟,而這些經濟提供的工作機會不穩定,幾乎沒有保障。目前,許多人正在動盪中返回家園,但從長遠來看,如果局勢進一步動盪,預計將有更多人再次逃離尼泊爾尋找工作,這將使印度本已不堪重負的非正規勞動力市場更加緊張。
正如巴什亞爾教授所說:“這種政治危機加劇了尼泊爾青年(失業)問題。毫無疑問,在印度的尼泊爾移民數量將會增加。與此同時,在印度找到合適的工作也並非易事。”
最終,對大多數尼泊爾人來說,邊境與其說是分界線,不如說是一條生命線——它為他們在印度提供了生存和機會,卻又將他們與家鄉的政治聯繫緊密地聯繫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