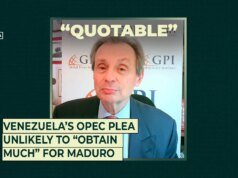我如何從內部與美國監獄系統作鬥爭
幾年前,在縣看守所時,我偶然發現了迪倫·托馬斯的一首詩,但我並不完全理解。上面寫著:“不要溫和地走進那個良夜……憤怒,對光明的消逝感到憤怒。”我喜歡它的節奏和緊迫感。但我還不知道從野獸肚子裡發怒意味著什麼。我很快就會知道。當教育還不夠時,我在新澤西州卡尼的哈德遜縣懲教中心被單獨監禁時開始學習法律。 25 歲時,我受過良好的教育,具備街頭智慧,遊歷廣泛,博覽群書,擁有並經營著一家成功的手機和筆記本電腦銷售企業。儘管如此,我還是無法理解法庭上的行話。聽起來像是一種奇怪的語言,其他人都說得很流利。我問了我的律師一些問題,但我沒有追問。我是新來的。我信任他們。這是一個至今仍困擾著我的錯誤。如果我知道我現在所知道的,我會在法庭上堅持採用不同的策略來打官司。如果我這樣做了,我不相信我會被連續判處兩次無期徒刑——150年監禁。你看,這個制度希望你坐下來,閉嘴,遵守規定。但每一次失誤都會像套索一樣掛在你的脖子上。當你的律師失敗時,如果你試圖上訴,法院的出發點是“健全的審判策略”,這意味著他們相信辯護律師一開始就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工作。走進法律圖書館:沒有救世主,只有策略2005年我到達特倫頓的新澤西州立監獄(NJSP)時,一位年長的囚犯告訴我,“你的工作就是遠離麻煩,生活並為你的生命而戰。沒有救世主。去吧法律圖書館並學習。”因此,我加入了囚犯法律協會 (ILA),這是一個由囚犯管理的律師助理團體。他們對我進行了培訓,我成為了一名未經認證的律師助理。加入 ILA 後不久,我開始了自己的法律鬥爭並開始幫助他人。我的第一次勝利是一項程序動議,幫助一名獄友重返法庭。那段記憶仍然像獎杯一樣留在我的腦海裡。幫助別人讓這場鬥爭變得值得。在聯邦人身保護法庭上,我又贏得了一場胜利,我想在那裡挑戰我的信念。我的請願被駁回。但我上訴了。我相信我的研究。我提交了。我贏了。結果並沒有維持下去,請願後來被駁回。但短暫的勝利意味著一些事情:我們可以反擊。 (馬丁·羅伯斯插圖)監獄背後隱藏的抵抗這是一個自訴訴訟當事人的生活——自訴在拉丁語中的意思是“為自己”——一個在法庭上代表自己的人。擔任自己的法律顧問很少是一種選擇;更多時候,這是必需的。我聘請了自己的律師,州政府指定了第二位律師來負責我的審判和初步上訴。在那之後,我就只能靠自己了。我無力承擔進一步的法律代理費用。我並不孤單。被監禁的人每年都會提出數以萬計的自訴動議。美國法院 2000 年至 2019 年的數據顯示,91% 的囚犯提出的法律質疑都是自行提出的。這並不新鮮。 20世紀90年代中期司法統計局的一份報告顯示,當時州囚犯提交的聯邦人身保護令申請中,93%也是自訴。這些數字證實了我們所看到的情況:法律代理在幾乎第一次上訴後就結束了,除此之外,我們只能靠自己,沒有培訓,資源有限,障礙重重。來自地下法律界的聲音以馬丁·羅伯斯(Martin Robles)為例,他是一位52歲的波多黎各人,他花了近30年的時間入獄多年。一旦他不再指定律師,馬丁就負責他的上訴。 “法院不遵循自己的規則,”他告訴我。 “他們不像我們那樣追究檢察官的責任。我們因為遲到一小時而受到時效限制(並且上訴被拒絕)。但是檢察官呢?他們有無限的迴旋餘地。”法院不關心囚犯在與律師助理溝通或研究判例法以準備法律摘要時所面臨的困難。執行所有這些操作的法律圖書館的訪問權限受到限制。在宿舍每週輪換期間,我們必須申請通行證才能進入圖書館,但通行證數量有限,有時我們要等幾週才能進入圖書館。法院通常會對囚犯施加同樣不可能遵守的最後期限,但卻沒有給予監獄限制任何自由度。例如,一位朋友有一個月的時間提交法律摘要,但在此期間不被允許進入監獄圖書館,因為他的手臂上打著石膏,這被認為是一種可能的武器。但由於無法進入圖書館,他無法獲得律師助理的幫助,無法查閱法律參考書,也無法使用電腦輸入摘要。截止日期已過,他寫信給法官講述了他的困境,但沒有得到延期。馬丁已經把他的憤怒變成了富有成效的事情。 “我將在 NJSP 開設第一門西班牙語法律課程,”他說。 “這是自願的。我是為了人民。我厭倦了他們被利用。”當金錢買不到保護時,39 歲的卡西夫·哈桑 (Kashif Hassan) 進入了系統,獲得了碩士學位,並聘請了私人律師。 “我向律師扔了錢,並認為我很好,”他說。 “但我受到了操縱和束縛。我沒有儘早戰鬥。” 最終,卡西夫拿起了法律文本並掌控了他的未來。 “我的第一個勝利是縣(監獄)的保釋動議,”他說。 “如果你不抗爭,沒有人會抗爭。如果你知道自己在做什麼,自訴訴訟就會有效。但法庭對待我們就像業餘愛好者一樣。就像我們不重要一樣。” 一位沒有準備辯護的律師湯米·科斯科維奇 (Tommy Koskovich),47 歲,在高中時被捕。 “我的律師嘲笑我,”他回憶道。 “他說公設辯護人辦公室沒有給他足夠的報酬,所以他沒有準備辯護。當我拒絕認罪協議時,他說,‘我沒有為你準備辯護。’”湯米隨後失去了所有上訴,但他現在正在尋求他唯一剩下的選擇:推翻他的判決和寬大處理的動議。他還通過新澤西州新的寬恕倡議申請了後者。在整個過程中,湯米學會了識別法律問題。 “有時,法院只會在你提交自訴書後才會認真對待你的問題,”他說。 “州訴科默案就是這樣發生的,一名囚犯自己提出了這個問題。” 2000 年,17 歲的詹姆斯·科默 (James Comer) 與另外兩人一起進行了多次武裝搶劫,被判犯有重罪謀殺和其他罪行。他被判入獄直至 85 歲。他很可能會死在監獄裡,但他與律師一起向新澤西州最高法院提起訴訟,並被重判。他在服刑 25 年後於 10 月獲釋。馬丁、卡西夫和湯米反映了我們許多躲在牆後的人已經知道的事情:這個系統不是為了正義而建立的,而是為了定罪而建立的。一旦你最初的上訴結束,你就得靠自己了。你犯的每一個錯誤都會受到懲罰。每一次失誤都會把門關得更緊。法律鬥爭也是道德鬥爭,但我們還是鬥爭。我們在搖曳的燈光下坐在破椅子上寫作。我們教其他人如何提出動議、了解判例法和解讀法律術語。 至於我,我正在製定一項 DNA 測試動議,以證明我的清白,以及一項撤銷刑期的替代動議。但新澤西州最高法院有幾個案件正在審理中,這可能有助於我的案子,所以我正在等待他們的結果。因為我們不會保持沉默。我們不會溫和地進入那個良夜。我們憤怒——反對錯誤的定罪、冷漠的法庭和希望我們放棄的製度。我們憤怒,即使沒有人在看。即使沒有人相信。即使勝利很小。畢竟,憤怒是希望的動力。這是故事中的第一個故事。該系列由三部分組成,講述了囚犯如何通過法律、監獄的喧囂和來之不易的教育來挑戰美國司法系統。
已发布: 2025-12-01 10:26:00